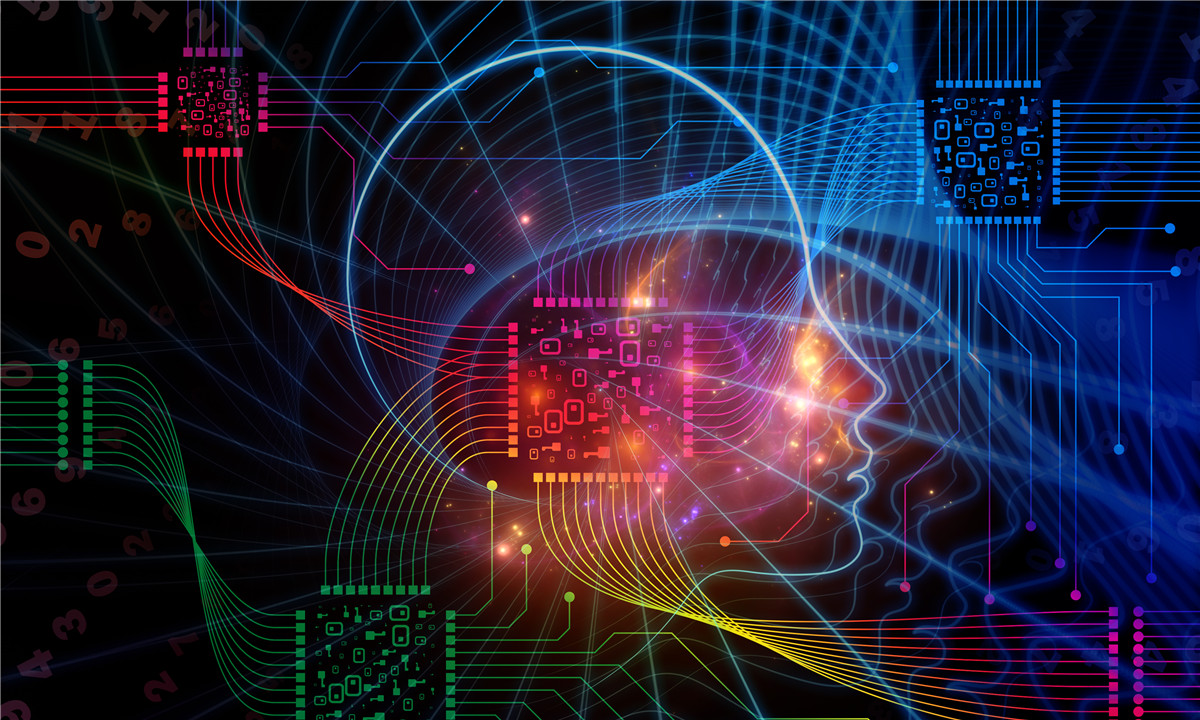猎云网3月13日报道 (编译:福尔摩望)
猎云网注:曾经,反主流文化让硅谷汇集了科技家、艺术家、活动人士等等人才,但是现在,金钱的力量让曾经理想主义盛行的硅谷变得物质化,丢失了想要改造世界的美好理想。
1992年1月14日,成千上万的艺术家、技术人员、政治家聚集在旧金山的金门公园,手举反主流文化的标语标识进行抗议活动。此次抗议活动被称为“硅谷事件”,而同样性质的抗议不曾在任何一个行业里出现过,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这项组织者称为“Digital Be-In”的活动是从1967年的“Human Be-In”活动演变而来,那项由Allen Ginsberg和Timothy Leary组织的活动据称是嬉皮士运动的高潮。“Digital Be-In”活动在当时被Soledad O’Brien描述为“90年代的网络文化与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的碰撞”,虽然这项活动并未在当时产生广泛影响,但是积水成流,这项活动最终导致了数字领域的创新:从虚拟的现实的构想转变成奇特的信息技术新形式,即现在的互联网。
声援这项活动的社会名望遍及很多领域。来自夏威夷的著名心理学家、迷幻药提倡者Leary以电话的方式声援了此次活动。旧金山的市长Willie Brown也出现在了活动现场。到现场声援的还有Ceosby Stills NAS & Young的摇滚乐手Todd Rundgren和Graham Nash。当然最高调的赞助商莫过于苹果公司了。
Digital Be-In的组织者Micheal Gosney(Verbum杂志的创刊人)在Pando的Don’t Be Awful集会上说道:“很多人并不怎么了解这个时代,因为对于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来说,互联网时代只是数字时代的开始。但是数字时代早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而就像很多技术演变的阶段一样,它们都是极受湾区文化的影响。而反主流文化与网络文化运动的联系是相当紧密的,可以说正是反主流文化催生了网络文化运动。我们所组织的Digital Be-In活动则是这种联系的一个具体体现。”
Digital Be-In活动里混杂了药物、舞蹈和技术,让人联想到Burning Man活动(Burning Man是由一个名为“Black Rock City,LLC”的组织发起的反传统狂欢节)。但是Burning Man活动更像是为硅谷精英量身打造的昂贵的精神释放盛会,帮助他们从固定工资、监视美国等等无聊的科技CEO生活里解脱出来。
而Digital Be-In活动并没有收取任何活动费用,它是一个真正包容的盛会,它把企业员工、年迈的嬉皮士、编程怪才以及活跃的活动人士汇集在一起。而这种活动最重要的部分是,它并不是为了逃离现实的数字世界,而是为了庆祝这个世界潜在的力量。在Burning Man里,短暂逃离了现实的人们不顾一切的去发泄,而参加Digital Be-In活动的参与者则相信科技的力量,相信科技公司,可以把人们团结在一起,能够提高人类的意识促进情感。当然,这听起来有点俗气有点幼稚,似乎像是居住在Golden Park里的90后们的梦想。但是与充满性别歧视和沉闷氛围的Crunchies活动相比,Be-In给我们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在旧金山参与组织了多次Digital Be-In活动的街头派对组织家Laird Archer说:“活动时所有人的关注焦点是互联网会让我们联系的越来越紧密。”Archer对于举办活动可是行业内数一数二的,他曾经帮旧金山的市长在“Fun,Sex,and Music”平台上竞选过。
Archer继续说:“我记得我是在Love on Mission街的地下室遇到了Timothy Leary。虽然现在的管理者已经变成了Denny,但是这种对待数字科技的希望会继续吸引着众人。”
想象一下,在2015年,政治家、企业家、艺术家、活动家、嬉皮士以及大型公司会聚集在一起合力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吗?显然不可能,这也引发了我们的一个思考:为什么这种以技术作为驱动的合作梦想不再存在了?
科技不再嬉皮士
2013年年末,在西奥克兰,通往搜索引擎巨头谷歌Mountain View郊区办公区的道路被一群活动人士堵塞了,他们举着标牌大声喊道:“谷歌滚开!致技术人员: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们!”他们还朝员工大巴扔石头,其中一块砸碎了大巴后窗。
这样的示威活动贯穿了2013年和2014年,活动人士在道路上堵截企业巴士,而这些巴士就如同公共巴士一样,将科技工作者从城市运送到郊区工作区上班。那么到底是什么促使了这些20年前积极参与Digital Be-In活动的活动人士开始如此暴力的反对科技产业呢?
原因其实很多,但先让我们从巴士讲起。通过这些巴士,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可以让他们的中上层技术员工方便的居住在旧金山的文化区域,而不是公司总部所在的拥堵的硅谷郊区。而让很多人不满的是,这些公司巴士无偿的使用城市公交车站来接送员工,虽然在经历大范围抗议后这些公司开始为使用这些公交车站交税,但是依然引起很多人的不满。
在一般情况下,科技人群的涌入稀释了反主流文化群体,更不用说在更糟糕的情况下了。但是这只是其一,大量高薪工人的涌入,已经给房市造成很大影响,而房屋租金也开始受此影响大幅上涨。
截止去年11月,旧金山一室公寓的租金中位数为3350美元。正由于这样的原因,许多长期居住于此的居民不得不离开。而某些“幸运”的住户受租金管制的限制可以继续居住,但是房东们却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有时甚至公然违法来驱逐住客。
由此可以看出,与Gosney和Archer所设想的会给旧金山带来各种好处的科技乌托邦所相对的是,很多城市开始限制房市,而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和反主流文化群体很难再城市里生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些人帮助实现了区域的技术革命。而当初并没有站出来声援的教师群体、社会工作者群体以及非技术工人群体,如今也不得不在飞涨的住房价格下苦苦挣扎。
许多人认为,这种所谓的“反技术运动”并没有发展起来,示威越来越少,而类似Valleywag这样的博客所提倡的“市政官员和过时的法规才应该为科技公司导致的生活费用的高涨负责”的想法被公众广泛接受。但是虽然公众示威活动已经减弱,但是对大型硅谷公司的厌恶和愤怒还没有消散。歌手兼作曲家Candace Roberts在“Not My City Anymore”里就攻击了科技产业的收购问题以及性骚扰问题。
然而,这种针对技术工人的敌意却是相互存在的。2013年,有两个年轻的创业者发布了一些引起争议的推文。创建了Celery支付网站的Peter Shih在一篇推文中嘲笑了城市里的流浪汉,还使用了歧视女性者使用的“49ers”暗指旧金山的女性(49ers形容低下层的女性故作上层社会女性)。
之后,Greg Gopman在Facebook上称流浪汉是退化的人类,不应该存在。而Gopman对社会所做过的最重要的贡献就只是组织过几场没有什么知名度的黑客马拉松。
Gopman和Shih攻击流浪汉的行为不仅揭露了他们病态的缺乏同情心的心理,也表明了城市里贫富差距日益严重(Rwanda最近的一份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
更重要的一点是,如今的科技企业已经抛弃了当初反主流文化的根。下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根据外国科技媒体报道,苹果、谷歌等很多硅谷公司串通起来压低了超过100万技术人员的工资。
而谷歌多年来一直与承包商和联邦机构保持紧密联系,为美国提供监测和军事设备等等,谷歌等技术企业还从事了营利性的监视工作。
那么为什么旧金山的科技企业会推崇Uber、抹黑编辑、盛行性别歧视、对司机的背景检查要求过低呢?
科技运动早期所具有的代表反主流文化特征的同情心、团结和责任早已让步于老旧的企业资本主义,这也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和使用方式。比如Facebook,它的终极目标并不是让人们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之所以这是给我们的直接感受,但是这纯属偶然,只是产品的副作用罢了。Facebook的终极目标是尽可能的吸引更多用户的关注,以便公司能够有效的投放广告给特定用户。是的,Facebook是可以帮助你重新联系上老朋友,但是让我们面对现实:用户所投入在Facebook上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刷新客户端、点赞以及比赛玩Candy Crush。
Gosney说:“我意识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们创造出令人惊奇的社交媒体,里面包含了我们所有的关系和个人身份,但是却只有一家公共公司管理。”

当理想遭遇利益
那么是什么导致原本起源于迷幻剂、活动人士和社区的科技时刻变成了公司一家独大呢?
答案显而易见:金钱。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人会认为互联网可以致富。本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使很多人遭受到了经济问题,只有一些百万富翁能够谨慎的察觉到危机提前撤资,才明哲保身。由于无法保证名利,互联网和数字科技一直以来吸引的都是那些具有创新意识、格格不入、希望发明未来的人,而不是那些投机者。由于与利益直接冲突的可能性较小,这种崇高的理念让Allen Ginsberg比Andrew Carnegie获利更多。更重要的是,没人会想到他们通过互联网可以收获极高的利润。
James Currier(猎云网编辑君注:James Currier是PayPal的顾问,yeshiva咨询投资公司Ooga Labs的CEO兼创始人,他早在90年代初就开始在硅谷打拼了)说:“反主流文化运动关注的多是一些微小的事物。”
“25年前,20年前,精通产品设计的极客们的任何一个细微的观点都会吸引个性品牌的注意力。这些极客都有一些共同点:他们能够很好的吸收新想法、处理问题,他们的效率很高,他们对于创新有着很高的要求。试想一下,如果当时是金钱将这些人聚集在一起,那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将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而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博客领域,或者称之为“互联网内容创作”,以前只属于爱好者的天地,现在突然变成有利可图的肥肉。最早一批在网络上创作文章的Awl’s Alex Balk在一篇名为《My Advice To Young People》的推文中总结了这个演化周期。他建议年轻人去寻找一块没人关注没人过问的领域,就像本世纪初的博客领域一样。在这个领域里,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制定规则和礼仪。如果投机者因为他们最终找到了如何赚钱的方法,而嘲笑你过早投入这个领域并摧毁你曾经建立起的一切时,请不要惊讶不要冲动。
但是,真的是金钱摧毁了硅谷反主流文化的根源吗?难道创造者的发明能够改变世界就一定要要求他们不以金钱为目的吗?赚钱又有什么错呢?瞧瞧Mark Zuckerberg捐了很多钱给慈善机构!
Mitch Altman在硅谷从事黑客数十年,这些问题一直存在于他的心里。他在Don’t Be Awful里说道,他发明了一种产品,可以在公共场所禁用任何电视设置。按照他的解释,该产品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实际上,他从2004年开始,所有的生活成本都是来自于TV-B-Gone里获得的利润。也就是说,在他的职业生涯里,利润一次又一次的直接冲击了他原本发明该产品的动机。
我第一份暑期工作是在一家制作适用于苹果二代电脑的计算机游戏公司,记忆有点久远,不过很开心很快乐。但是随后美国军方出现,想要把我们的游戏修改成杀手直升机训练模拟器,并支付给我们一大笔钱。我的老板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公司可以从中获利颇丰。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我选择了退出。在我发明TV-B-Gone之前,我是一家硅谷创业公司的创始人,这家公司主要生产硬盘控制卡(我们称之为RAID控制器),这种设备可以增加存储容量提高运行性能。这一次美国军方又来了,还带来了特勤局,他们想使用这些存储系统来存储他们监视我们所搜集到的所有数据。他们愿意为此支付一大笔钱,之后风投公司就接管了我所创办的公司,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赚大钱的机会。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又一次,我选择了退出。
不论你是否赞同Altman对美国军方的估测,但是你不得不佩服他的信念,因为这种信念在任何行业都是很罕见的。但是这种所谓的道德信念更多的出现在个人身上,而几乎不会存在企业里。对于企业来说,利润并不是一种在创新过程中会偶尔出现的愉快的副作用,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原因,这也是利润为何会变得如此可怕的原因。
“如果一家公司可以通过支付罚款和诉讼而不是制造一个撞击后会爆炸的汽车获取更多的利润,那么福特汽车公司将会再一次遭遇到上世纪70年代的Pinto问题(猎云网编辑君注:Pinto存在油箱爆炸问题)。而他们为受害者家庭诉讼支付的费用要少于他们重新设计汽车的费用。”
但是与之相反的是,Mitt Romney认为企业不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是由一个个个体组成的,这些个体里就会存在像Altman这样的道德约束。
“所有这些组织都是个体的集合,组织所做出的决定都是来自于这些个体,只要他们选择,这些个体就可以决定不去做那些让他们以及周围的人的生活糟糕的事情。即使这样意味着会失去工作,这也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值得花时间细细考虑。”
Uber CEO 需要嗑药
所以我们该如何把反主流文化(包容性、同情心等等)重新带回科技领域呢?我们该如何确保非科技人士(艺术家、活动人士和各工种工人)可以一起参与塑造未来呢?
其实举办像Don’t Be Awful24小时集会就是一个好开始。在这个集会里,任何人都可以演讲三十分钟,参与过的演讲这有反拆迁人士Erin McElroy、风险资本家David Hornik、嬉皮士发明家Mitch Altman、编辑Jose Antonio Vargas、建立硅谷的元老Tim O’Reilly、来自不同领域的企业家(比如合乘领域的Nick Allen和约会领域的Amanda Bradford),我们甚至还邀请了最犀利的评论家神秘人Richard Bottoms来做演讲。
当然让这些代表不同利益的人进行对话并不能保证理想主义能够回归科技产业,但是这只是第一步。剩下的工作就像Altman所说的那样,必须由个体来完成。科技工作者能愿意冒着失业的风险坚持正确的事情,就像那些勇敢站出来揭露苹果薪酬丑闻那些揭发者一样。编辑、活动人士和艺术家能够有勇气向科技公司说出他们的不满,吸引公众目光。开发人员和决策者要能够拒绝快速盈利和风险投资的诱惑,沉下心来取制造产品。而公司要能够线上线下都保证社区的安全性和理智性。
有研究表明,反主流文化的首选药物LSD有助于提高同情心。在“混蛋文化”盛行的硅谷,也许企业家们应该停止服用Soylent这样的药物而是体验另一种。你能够想象如果Travis Kalanick嗑药了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吗?
Source:Pando
想要了解更多创业创新知识,快速添加猎云网微信号:iliey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