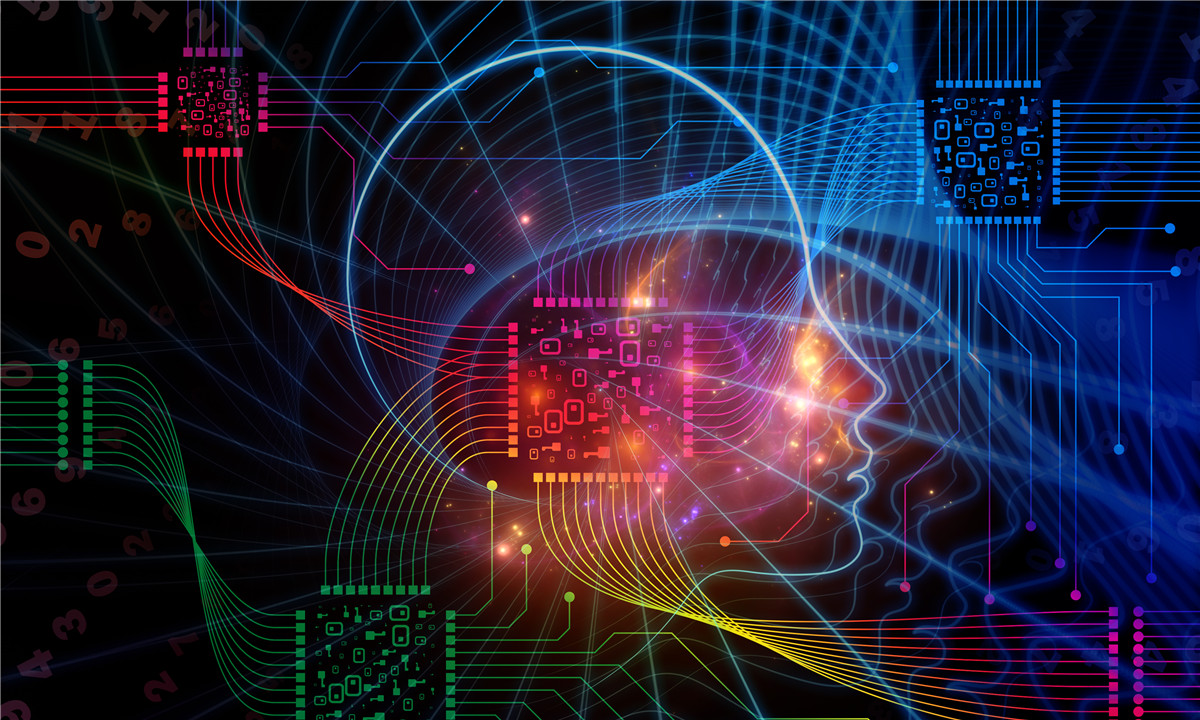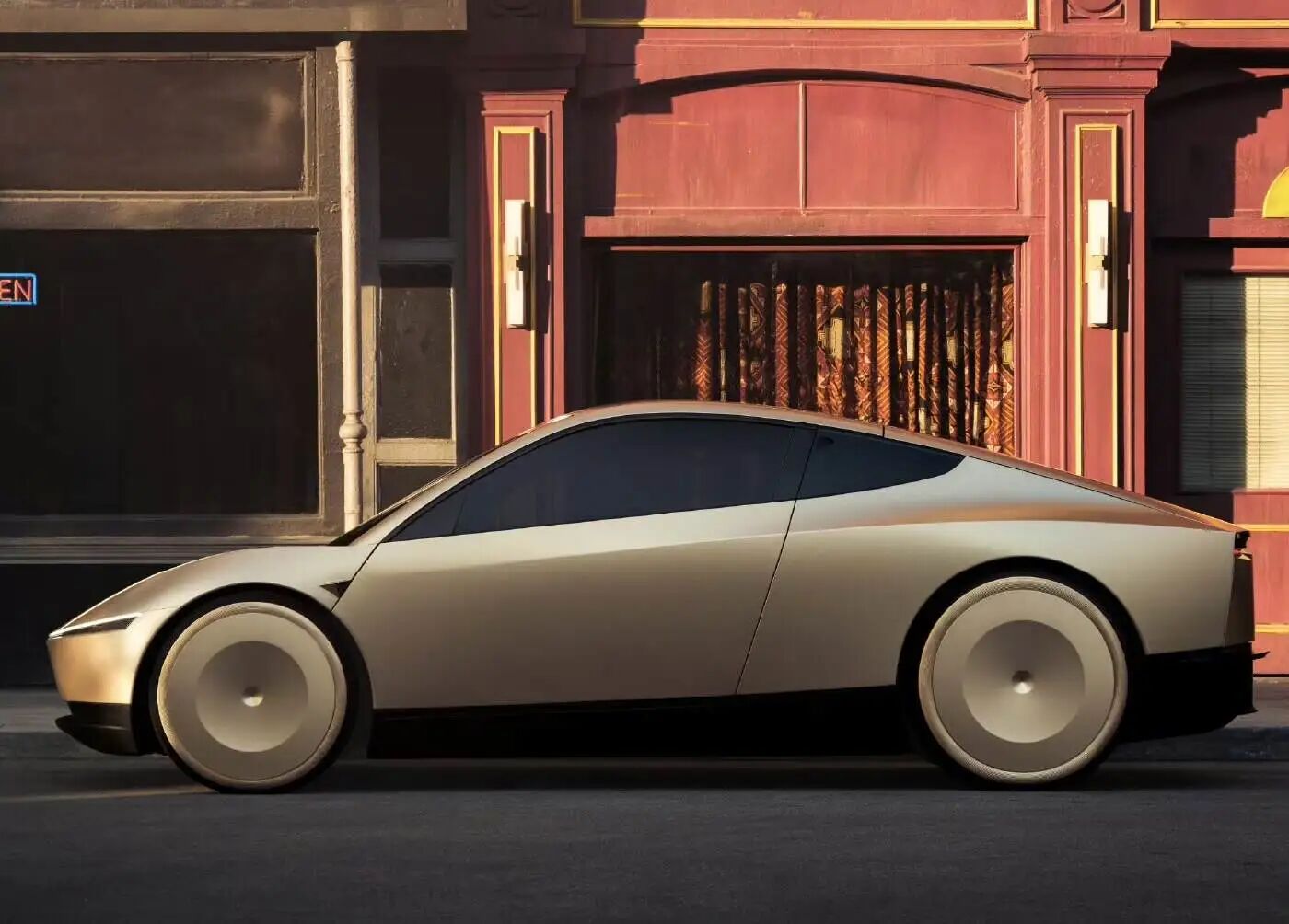本文来自合作媒体:饭统戴老板,作者:饭统戴老板。猎云网经授权发布。
科学界最著名的两大期刊,一个是1869年创刊的《Nature》(自然),一个是1880年创刊的《Science》(科学),能在这两个杂志上发表论文,基本上就等于叩开了国际顶级学术圈的大门。但少有人知道的是,中国人第一次在顶级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时间,是1881年。
1881年,《Nature》杂志发表了一篇来自中国的论文,名字叫做《声学在中国》。论文对著名的伯努利定律提出质疑,并用现代的科学矫正了这项古老的定律。对此《Nature》编辑部高度评论道:“我们看到,对一个古老定律的现代的科学的修正,已由中国人独立地解决了。”
这篇英文论文其实是翻译自一篇拗口的中文论文,叫做《考证律吕说》。论文的作者徐寿生于无锡一个地主之家,少时研究经史百家,但在童生考试不幸折戟。落榜后的徐寿深感“学八股救不了中国人”,索性放弃了科举做官的发展道路,他开始涉猎数学、物理、化学等书籍。
时值晚清洋务运动高潮,徐寿在1867年来到曾国藩治下的江南制造总局,向后者呈送了四项建议,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翻译西书”。在曾国藩的支持下,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挂牌开馆,徐寿主导推出了《化学鉴原》、《化学考质》、《法律医学》等译著,并创造了汉字命名的化学元素。
1874年,徐寿与英国传教士傅兰雅联手创办格致书院(现为上海格致中学),座落在上海广西北路66号,是一所完全新型的近代学堂,主讲矿物、测绘、制造等课程,称得上是一个西学传播的中心。后来徐寿在《Nature》上发表的论文,英文版便是由傅兰雅操刀翻译。
在发表论文3年后,徐寿便因病逝世。其创办的翻译馆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坚持了45年后,以“翻译西书又造不出大炮”为由,被时任北洋政府一把手的段祺瑞下令关闭。从《Nature》发表徐寿论文的1881年,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中国科学研究在大段的时间里都只有留白。
究其根本,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顶层设计、官僚机构、社会组织、人才梯队的密切配合,更离不开财政的投入、金融的润滑、商业的造血和普罗大众对科学精神的尊重。几位昙花一现的科学天才是弥足珍贵的,但难以撼动历史的车轮。
从五四喊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那刻开始,“科学强国”成了几代中国人持续奋斗和努力的目标。而在一百年多年后的贸易战里,我们又觉得之前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在当下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我们也有必要去复盘,在与历史赛跑的百年中,我们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
或者简单的一句话来说:中国离科技强国到底还有多远?
李约瑟之问:基础投入的历史赛跑
这个问题不光中国人在问,外国人也在问。最早在西方学术界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中国科技史界的“白求恩”——英国人李约瑟。
李约瑟(Joseph Needham)是英国一名生物化学家,毕业于剑桥,很年轻时就名扬学术圈。他在37岁那年接待了几个中国留学生,听闻了他们的介绍后便对中国古代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随后李约瑟开始学中文,并先后十几次来到中国,走访3万多英里,最终撰写了大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可以说李约瑟通过大量的考据、发掘和整理,系统性把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展现给了西方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带来了科技自信,但与此同时,他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略感羞愧的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李约瑟之问”的答案很多,有人从思想文化角度找答案,有人从政治体制角度找答案,各自有各自的道理。但如果从纯科学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科技过分强调实用性,技术基本上都是经验技术,属于工匠文明,缺乏理论层面的探讨,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社会自上而下对基础科学是忽略的。
以火炮为例,这种冷兵器时代杀伤力巨大的武器,理应被统治阶级投入无数精力来研发和改进,但一直到清朝,中国人对火炮仍然“只知道用铁铸成炮身,全无科学分寸,所以施放不能有准头”[5],相比之下,欧洲则沿着火药、机械、冶炼等方向深入至化学、物理、材料等学科,成果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洋务运动以来,这种情况逐渐被精英阶层所了解,但近代动荡不安的环境,让救亡图存成为民族的第一要务,科学研究的优先级显然只能往后排。建国后大部分资金也都投向工业化环节。尽管依靠着科研人员的努力,我们依然在60年代合成了牛胰岛素、在70年代合成了青蒿素,但“一花独放不是春”。
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快速发展,“下海”成为了社会时尚,一批批基础研究人员也转向了应用研究,也就此有了“做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原本就薄弱的基础科学,再遭冲击。一些高校甚至连先进图书资料都无力采购了。基础科学危机日益严重,老一辈科学家、教育家们和技术官员们急在心里。
尽管“前三十年”建设的高校和研究所遍布大江南北,国务院也在1986年也批准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但这些机构的运转需要强大的财政来保驾护航。实际上直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每年拨给基础科学的资金才有了长期保障。2001年入世之后,GDP和中央财政连续飞天,中国科研逐渐走出寒酸窘境。
到了2018年,中国每年发表的SCI总量已经高达全球第二,但同年爆发的贸易战却又冷酷地告诉我们:所有的“卡脖子”,归根结底都是基础投入不足。
在大洋彼岸“总倒逼师”的驱使下,全社会对贸易战暴露的短板都进行了系统性反思。2019年袁亚湘院士曾直言中国重技术大于重科学,基础研究投入严重不足。而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基础研究费用在全年总研发支出中仅占5%,这还是过去10年最高的比例,而同期美国是17%,日本是12%。
“基础研究突围”的必要性已毋庸置疑,而和美国占总投入20%的社会资金相比,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国家队,也有企业队。
中国企业家在仓禀充实之后,大都开始向具备社会价值的领域倾注资源,有的投向慈善,有的投向扶贫,这即是西方思潮的作用结果,也是传统“达则兼齐天下”的理念体现。而很多头部企业在意识到基础科研的重要作用之后,也开始逐渐向“科学”这个以前少有民间资金参与的领域列队进发。
在2019年两会期间,红杉的沈南鹏和腾讯的马化腾不约而同地提交了“引导社会力量,加强基础科研投入”的提案。其实不光是红杉和腾讯,华为、阿里、百度、吉利、恒瑞等企业这些年都加大了对基础科研的支持力度,不仅在内部投入巨额资金搞基础研发,跟外部的高校和研究所也有大量合作。
杨振宁曾说过:学者获得博士学位后5-10年,正是一个困难时期,要选择一个领域,做出一个站得住的工作。但这段时期恰恰又是买房、结婚、子女教育等人生重大开支高发期,2018年5月,在腾讯集团总部38楼,北大教授饶毅在餐桌上向马化腾讲述了青年科学家面临的压力,马化腾和饶毅仔细讨论后,留下了一句话——“我找团队跟进”。
二十多天后,马化腾在北京的未来论坛上强调“不能再抱侥幸心理,一定要投入更多资源做基础科学研究”。那年11月,腾讯20周年之际,马化腾和饶毅、杨振宁等科学家共同设立了“科学探索奖”,资助青年学者。
这个有“中国诺贝尔奖”之称的奖项面向九大基础科学和前沿核心技术领域,不计报酬的鼓励青年科学工作者。所有科研成果不以商业诉求为目标,“科学探索奖”的资金,也完全由科研人员自主支配。
我们总是会纪念为科技奉献青春的老一辈科学家们,感叹他们的无私付出。然而,如果一味要求科研人员必须喝冷水、啃干粮,显然是不科学的。正如马化腾所说,“我们做应用创新,就是在科学家拓展的疆土上去建楼”。重视基础研究,让科研人员可以安心做研究,应该是一种社会共识。
对于擅长“造节”的中国人来说,我们除了各种消费节外,也应该多去创造“科学周”、“科学月”、“科学季”这种属于“赛先生”的节日。
钱学森之问:人才梯队的百年大计
2005年7月,在医院休养的钱学森,对前来探望的温总理进言,“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个话题在2009年钱学森去世几天后,再次被安徽高校11位教授抛向了社会,呼吁大家直面这个沉重,却不容回避的“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直指人才建设,这也是百年中国教育界绕不开的难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高校里有德国教研模式、美国选课模式、英国书院模式;但建国后则基本都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进行的。从微观教学细节,到中观高校架构再到到宏观管理体制,可以说都是苏联的影子,甚至教材都是苏联蓝本。
1956年,苏联专家为我国编写了629种教材,培养研究生和进修教师8万多人[6]。苏联模式下,所有教育都以国民经济需求为根本,形成了高度集权的计划模式、高度专门化的教学体系。定向招人、定向学习、定向分配。这种方式下的高等人才,如螺丝钉般,整齐划一,指哪儿打哪儿。
这个模式有助于快速定向攻坚,但弊端也逐渐显现。在定制化的前程下,学生就更功利主义、少了追求自我的动力。就如张艺谋当年考大学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包分配。只要是大学生出身,地位就不一样[7]。”而比起个人选择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世界发展充满各种可能,定向化的模式,难堪创新大任。
2019年,正处于贸易战旋涡中的任正非接受央视采访,也出乎意料地重点聊了基础教育制度的不足。任正非的父亲任摩逊一生投入乡村教育,对基础教育的很多问题十分敏感,在采访中他讲出了“一个国家的强盛,是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完成的”和“中美贸易根本的问题是教育水平”这样的金句。
任正非也曾谈及华为对于科学家的定位,基础研究与商业化的关系等问题——“高科技不是基本建设,砸钱就能成功,要从基础教育抓起,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
数学大师丘成桐对于国内的高等教育,也曾发出过类似的感慨,第二届丘成桐大学生数学竞赛决赛期间,丘成桐在接受采访时说:“老师们只注重所谓的研究,没有好好地带学生。竞赛结果显示,有些名校学生并不行,有的不那么出色学校的学生,反而成绩还好些。这样就能看明白,哪些学校是下了工夫的。”
丘成桐一直坚持并倡导“培养和发现人才应从中学开始”的教育理念,自2008年开始设立丘成桐中学生数学奖。它区别于普通的科学竞赛:面向全球华人中学生,倡导创新思维和团队合作,舍弃试卷和标准答案,让学生以提交报告的形式参与竞赛,旨在推进中学科学发展,激发和提升全球华人中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和创新能力。
2019年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丘成桐的批评更加直白:中国高校仍是以应用为主、基础为副,结果有可能两方面都没能成功。中国的科技要领先世界,一定要“大力发展”像数学这样的基础科学,而不是“普通发展”。
而这些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看到了这个问题,毅然投身“百年大计”,典型的例子,便是施一公等科学家牵头创办的研究型学府“西湖大学”。
施一公是留美归来的清华毕业生,他也是美国国家科学院、人文与科学院的双料外籍院士。2018年,他在西湖高等研究院的基础上,牵头创办了西湖大学,希望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探索者、聚焦基础性、前沿科学技术研究。西湖大学是民间资本的一次重要尝试,建校资金捐款者就包括马化腾、张磊等人。
另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学习国外基金会的方式,来直接资助科学研究项目和青年科学家。这方面马化腾、张磊、李彦宏、马云、沈南鹏等企业家都已经做出表率,像科学探索奖、未来科学大奖、西湖大学等企业牵头的项目会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面向青少年的科学知识普及,则是一种更加长远的“科学基建”。
2013年,腾讯开始举办非商业化的WE大会。那年的WE大会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基普·索恩(Kip Thorne)给向他提问的青少年编辑讲了一个故事:在他四岁那年,祖父便告诉他要找到一个热爱的工作,干起来就像玩儿一样。在他13岁那年,读到了一本科学著作《从一到无穷大》,由此便爱上了物理,一钻研就是一辈子。
作为“互联网原住民”,当下教育体系弱化了培养青少年在基础科学上的兴趣和知识储备,很多互联网公司其实有能力也应该帮助青少年养成对科学的热爱和探索。
在那年的WE大会,就曾有不少小朋友拿着英文材料像海外科学家请教问题。如今,单场大会已经变成了WE大会、医学ME大会、科学探索奖、科学脱口秀X-Talk共同组成的“科学周”。
在基础教育领域,企业无法越俎代庖,但可以通过跟高校合作、捐助研究型大学、推动青少年科普等形式促进全民科学精神的养成。尤其是面对“z世代”的青少年,那些拥有亿万用户的“国民级”App显然可以有很多创新的行动和贡献。
无论未来能否成为科学家,让青少年喜欢科学、尊重科学都是一件“功在千秋”的时期。全民科学精神的重要性,已被疫情期间的大洋彼岸充分证明。
任正非之问:市场机制的开山凿路
2019年5月,任正非在接受采访时谈及华为遭遇的政治施压,称“过去的方针是砸钱,晶元光砸钱不行,要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但又有多少人还在认真读书?”
人大教授向松祚称之为“任正非之问[1]”,并将其与“钱学森之问”并列。美国新一轮极限施压之后,任正非不再密集接待媒体,频频对外发声,而是短时间内走访四所高校,大谈基础科研的重要性。
任正非曾提到过一个“不会谈恋爱,只会做数学”的俄罗斯小伙子,“他不善于打交道,十几年干什么不知道,之后突然告诉我,把2G到3G突破了。我们现在很厉害,与这个小伙子的突破有关。”
通过基础研究掌握源头科技,随后一步步外溢建立产业,几乎是每一个高科技强国发展轨迹的复刻。在这条路上,最困难的不是人才的培养,而是能够反哺科研投入的市场机制。
文一教授在《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中这样写道:市场是个昂贵的公共品。洋务运动期间5000万两白银的军工投资付诸东流,盖因产品无法创造利润,实现自我循环。改革开放时期,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为工业注入了劳动力和购买力,才能让工业化实现自我运转。
而华为能给博士开出200万年薪,核心是形成了一套“投资-研究-回报”的市场机制,比如华为的“2012实验室”拥有高达2万多名员工,遍布在全球十几个国家,涵盖通信、数学、材料等多个领域,里面到处都是“黑科技”,它们都被转化成华为产品上的创新,获得丰厚回报,形成闭环。
“2012实验室”的模式显然参考了AT&T当年大名鼎鼎的 “贝尔实验室”,后者是“投资-研究-回报”的集大成者,不仅培养出了11位诺奖得主,还孵化了晶体管、激光器、太阳能电池、发光二极管、数字交换机、通信卫星、电子数字计算机、蜂窝移动通信等新技术的面世和应用。
华为之后,阿里和腾讯相继成立了达摩院与量子实验室,标志着科技公司开始在基础科研上大举布局。
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科学基础设施的建设都由政府的财政支出来完成,在摘得无数硕果的同时,也造成了“重设施、轻人事”、“重顶层、轻基层”等问题,而究其根本,则是市场机制参与度不足,科学研究没有应用层面的方向指引,无法自我造血自我循环。
以当年“一个人吊打一所学校”的微软亚洲研究院为例,他们曾在2008年公布了12项“顶级研发成果”,其中数字墨水、语音识别、复合TCP、Halo图形等研究项目,几乎都在数年后得到了大规模应用。微软在商业上强大的造血能力支撑了这些科研项目,落地之后的科学研究又能反哺自身。
早在 2017年初,腾讯就开始进军量子计算。牛津大学量子物理学博士葛凌教授以腾讯欧洲首席代表身份加入腾讯,被认为是腾讯布局量子计算的开端。2018年初,香港中文大学著名量子理论计算机科学家张胜誉教授受邀加入腾讯。
量子实验室剑指处于雏形阶段,但又具备颠覆性潜力的量子计算,去年年中,量子实验室与外部科学家Iordanis Kerenidis合作一起对神经网络中最基本的前馈网络,研发了第一个可证明的量子加速算法。
今年5月的一场公开活动中,马化腾就公开表示,“中国在应用科学领域是处于全球创新位置的,尤其在互联网方面,但是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同为嘉宾的未来科学大奖科学委员会轮值主席季向东则表述的更加直白:这个社会环境得允许一批人做“无用”的东西,允许他去看天上的星星、看白云、看流水。
突如其来的疫情期间,“看星星、看白云、看流水”的意义已经得到了体现。
今年2月,一大批搭载“腾讯觅影”AI辅助诊断技术的人工智能CT被运往武汉方舱医院,可以对病人肺部和新冠肺炎病灶做了精确的自动分割,在患者CT检查后数秒完成AI判定,并在一分钟内为医生提供辅助诊断参考。在抗疫形势最严峻的时期,大幅度提高了诊断效率。
AI技术在医疗领域得到应用,其实是市场机制“强外部性”的绝佳体现:对科学科技的投入,有商业价值,也有社会价值,能够让前沿科技完成商业闭环,又能推动科学解决社会重大挑战,这是一种“可持续”的双赢,而这种“双赢”,又会给科学领域带来源源不断的资金、人才和成果。
对于长周期、高投入、回报未知的基础科研领域来说,华为“2012实验室”也已经趟出了一条可行之路,腾讯阿里百度也紧跟其后,未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参考这套模式。这是“大钱”,也是“长钱”。
以华为、腾讯、平安为代表的商业巨头,以及各路民间资本开始对科学领域的投入,为基础科研搭建适合的市场机制,是过去四十年商业繁荣和创业创新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在高科技领域更进一步的必经之路。
尾声:“科学强国”离我们还有多远?
1974年,为了缓解国外竞争压力,美国国会通过了《1974年贸易法》,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则是聚焦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案第301条,即“301条款”。近50年来,无论是老牌盟友欧洲、韩国、加拿大,还是阿根廷、印度、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几乎都遭遇过所谓的“301调查”。
不过301条款最主要的目标,则是彼时经济迅速崛起的日本。1975至1997年,美国共对日本实施过16次“301调查”[3],多数调查都以美国成功、日本被迫妥协让步而告终。
与美国频繁的贸易摩擦让日本国内“技术自立”的呼声越来越高,政府也顺势提出了“科技立国”的战略口号。1980年,日本通产省发布《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展望》,天量财政预算开始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倾斜。90年代后,通产省再度提出“告别改良时代”的口号,目标直指“科技发达国家“。
大力投入科研最显著的成果,便是日本“18年18位诺奖得主“的奇迹,而长期占科研经费15%比重的基础研究投入,也终于在十多年后的半导体领域结出硕果。
以半导体材料领域为例,日本企业在全球市场所占份额达到66%。19种主要材料中,日本有14种市占率超过50%。而在占据产值2/3的四大最核心的材料:硅片、光刻胶、电子特气和掩膜胶等领域,日本有三项都占据了70%的份额。最新一代EUV光刻胶领域,日本的3家企业申请了行业80%以上的专利。
在这个特殊的行业里,无论是提纯,还是配方,都需要极端的耐心和极致的专注。时常为了得到10%的效果改良,就需要几年的研究和试验。而这提升的10%,却影响着万亿规模的半导体行业。
单单用“拧五年毛巾“的工匠精神来概括显然不全面,究其根本,是8个诺贝尔化学奖带来的科研实力。
日美贸易摩擦和当前中国面临的情况极其类似,日本基础科研厚积薄发的历程,也是中国产业升级的必然选择:中国需要坚定决心,在科学领域持续投入,才能跻身科学强国。这个周期,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而未来要想引领全球创新,更是需要以百年来计的坚持。
一百多年前的1896年,洋务运动的成果被甲午战争尽数抹去,李鸿章在汉堡问了俾斯麦这样一个问题:用什么的方式,才能让中国跟德国一样强?
百年之后,中国已然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人尽皆知的“世界工厂”,中国的消费品牌开始远销海外。如今,中国的产业升级之路已经抵达了最后一站,我们还有距离,但怀揣希望。
摘得高科技皇冠上的明珠,四处办厂的洋务派思考过,“科技界白求恩”李约瑟思考过,学术泰斗钱学森也思考过,如今,这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今年9月在京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作为2019年“科学探索奖”获奖人之一的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在会上说:“经常有人问‘你的研究有什么用?’我曾在很难维持实验室的时候,也想过要不要去做热门研究。希望国家进一步引导不以‘有没有用’为评价和发展的基础研究……”
而这也正是“科学探索奖”设立的初衷:面向未来、奖励潜力,鼓励青年科学家潜心进行科学技术研究。
在贸易保护甚嚣尘上的当下,政府交流面临障碍,企业应该主动打破逆全球化的铁板,促进科学和人才的交流。今年的WE大会上,就有来自6个国家的7位全球顶尖科学家分享了天文、物理、生命科学等领域的科学进展。
而在基础投入方面,除了设施、设备、科研项目的投资,更应该重视的是对科研人员,尤其是基层与研发一线科学家的保障。无论在什么时期,人才都是一个国家最核心的资产。
总而言之,政府投入、民间参与、舆论重视、国民科学精神不断提高,科技“善”的一面才能超越竞争,造福社会。就像马化腾在首届WE大会上说的,“这次论坛没有谈及商业或者公司之间的竞争……我们谈的是未来如何用科技改变人类生活,如何解决我们可能现在想不到的未来的很多问题。”
2020年的疫情也在不断告诉我们:尊重科学、重视科学、投入科学,才能保持国家和民族的竞争力。只有沿着基础投入、人才建设和市场机制不断修炼内功,我们才会离“科学强国”越来越近。